在中国,自1982年宪法制定以来,宪法进行了两次重大修改:一是1999年修正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简称“法治入宪”。二是2004年修正案,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简称“人权入宪”。
1988年,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陈云生赢得声誉:成为中国进出口图书公司以原版出口日本的法学著作;系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图书馆唯一一本中文原版藏书;该书的压缩版和精练版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首次发表的法学和宪法学专论。
“新宪法作为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章程,确立了社会和国家重大的目标和治国的战略方针。”陈云生觉得,宪法学科需要重建,其他法学学科同样也需要重建,但各法律的制定都要依据宪法。
宪法学者许崇德曾将“八二宪法”的意义概括为“宪法重建”,法学界称之为“法治重建的起点”。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中,陈云生逐渐崭露头角,开始有了小名气。
“我们5个人24小时坚守岗位,不舍昼夜地写调研报告。当时都只能在办公室里简单休息一下,夜深了,我们自己买碗泡面吃。”陈云生回忆,当时找相关研究资料很难,“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从清华北大转来的图书,因多年没人看,灰尘都有一寸厚,我就把尘土扒开一点点地找”。
据陈云生观察,最近几年兴起了“违宪审查”的专题研究,“要解决中国宪法监督这一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单凭学术热情和强烈呼吁不能做到,必须首先从宪法学理上采取扎实而艰苦的步骤,任重而道远”。
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王叔文携领下,陈云生和其他团队成员承担了大量学术调研和资料准备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宪法学科始建于1958年,在国内宪法学界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宪法学的宿命注定要和国家最高权力打交道。”当时,陈云生极力主张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一提议经过宪法学界多代人的反复论证,最终在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设立。
“这种清楚、态度鲜明的表述,一方面彰显了中共中央对于宪法监督制度的认识,已经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及要在中国健全宪法监督制度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从宪法学术的角度上看,也是对宪法学术界在这个领域多年的学术探索和倡议的充分肯定和回应。”陈云生坦言,在学术生涯中,“如果能把这方面学问做到极致,也是一件能聊以自慰的幸事”。
在学术生涯中,陈云生长期致力于宪法学、行政法学、法人类学和法哲学的研究,亲历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宪法修改、宣传与研究,对宪法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等7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终身荣誉专家咨询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人生难百岁,法治千秋业。”这是一位法学长者的自我心境。新时代之下,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这一问题势必成为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考验。
值此新征程,澎湃新闻敬邀多位中国资深法学家分享法治经历、学术思想,记录他们的法学思考和作为,以此集成“论法的精神”专题,期冀为一个法学时代留下注解。
我国现行宪法制定于1982年,史称“八二宪法”,有着重要意义的突破。作为亲历者,陈云生认为宪法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宪法文件本身,更在于其核心要义——构建一个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人的尊严”镜像。
参加工作之后,陈云生便投入到“八二宪法”的制定工作中,这项工作的牵头人正是他的博导、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张友渔。
幸运的是,他所填报的最后一个志愿——北京政法学院最终录取了他,随即开启了法学领域的探索。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广西工作,但启程时接收单位发来电报说:“请暂缓报到。”在“文革”期间,陈云生暂时寄身平谷农村老家,这一住就是两年。在家期间,除了每天捡拾牛粪作为自留地肥料之外,别无他事可做,内心苦闷彷徨,时感前途渺茫,焦虑感与日俱增。
“它不光是个人努力奋斗的必然结果,更有赖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历史机遇的赐予。”陈云生认为,由谁成为第一位法学博士并不重要,如果说其中还蕴涵着某种意义的话,那就是中国宪法学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法学学科重建和发展历程中,曾占有一席显著的地位,“由宪法专业诞生中国第一位法学博士,虽非必然,但也绝非偶然”。
“做学问本身不要太多考虑学术影响力,那是政治和社会层面以及时人和后人是否认同和接受的问题。”陈云生表示,自己写的书可能要三五十年以后才有人有兴趣去深读,知道那时有一个学者做过这样的研究,“我不奢望这一代人都会理解”。
1982年,宪法正式通过后,全国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宣传活动。陈云生说,当时从领导到专家,每个人都投入到了这场宣传热潮中,“作为其中的一员,我积极参与撰写和发表有关新宪法的文章,除了百余篇报纸短文外,还广泛参与全国出版的新宪法宣传小册子的编写工作,数量不下几十本”。
彼时,学术界才开始真正具有宪法科学规范意义上的创作,比如北京大学龚祥瑞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武汉大学何华辉的《比较宪法》等著作。“因为八二宪法实施后,只是一个文本上的法律规定。但政府机关执行过程中是否秉持正义、是否符合理性、宪法的实施和监督机制是否科学,都需要继续研究。”陈云生因此投入到宪法监督理论的研究中。
宪法草案拟定后,经《人民日报》公开发布,三次征求公众意见。“民众参与热情高涨。”陈云生回忆,在全民讨论过程中,草案收集了三千多条意见,小到哪个字、哪个标点该用什么、怎么用,都有人提出。
在他看来,建立法治国家只是解决了治国方略的问题,至于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后续的一系列社会基础的改造和配套机制等问题,需要更深、更细的谋划与建构,其中最大的困难和挑战,莫过于适时地改造中国本土的法律文化的模式,以适应现代法治的生存和发展对法律环境的需要,“必须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即首先在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实现现代法律、宪法的启蒙,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建成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
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着力推进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在建立“违宪违法审查制度和机制”方面,作出了有原则性又有明确方向性的规划。
在探寻中国法治建设道路上,法学学者挺身而出,力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行政等治国方略,呼吁人权保障、司法公正、权力制约等法治理念,投身回答“何以法治”“法学何为”等时代之问,进而诠释法的时代精神。
放眼域外,宪法也被视为是最重要的法律。以美国为例,法院有权宣布违宪的立法无效。陈云生直言,“宪法至上”的学说已被全球各国广泛接受,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宪法比普通法律具有更高的法律地位,有的甚至规定宪法中的某些条款不能修改。
“宪法至上是先人留给我们的重要法律遗产。”在陈云生看来,中国古籍《尚书》中的《洪范》就是被视为“大经大法”的国家根本法,仔细研究表明:它与现代宪法既神似又形俱,宪法至上的观念早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就确立了。同理,西方所谓的高级法、基本法等也都含有至上的意蕴。
与此同时,陈云生还率先和积极主张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极力倡导人权保护。他认为,要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构更加完备的宪法实施与监督制度,并在此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制度体系的日益完善和强大。
此后,陈云生被调回县里,随后被派到农村担任县“基本教育工作队”的队员。1978年,在县里工作的夫人给他捎来信息:国家要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了。陈云生决定冒险报考,但留给他的时间却不多,“总共备考时间才有两个月,复试前一天,我还在火车上背诵教材,已然两天三夜未合眼”。
在现代社会,宪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从田间地头走上学术讲坛,陈云生以其宪法学术研究成就影响了后辈法学学子。“每一位立志于投身中国宪法学的学人都有责任为中国宪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他说。
两年之后,他始知可以报到。初到接收单位,行李未解,便接受组织安排下放农村,开始了两年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陈云生直言,起初很不适应,但经过半年多的磨炼,终于可以同当地农民一样光脚走碎石路、下水田扶犁插秧,还能挑一百来斤的水粪担子走在狭窄、湿滑的田埂小路上,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在广西农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耐得住饥苦和劳累,意志也因此变得更加坚韧,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够坚持下去”。
现代宪法通过法律文本和司法实践确认了其至上的法律地位。陈云生表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着两大紧急任务:一是拨乱反正;二是重建国家政权机构,这两者都离不开新宪法的制定,新宪法适应了新的历史阶段,并能对其加以确认和规定。
前两年,年逾八旬的陈云生得了一场大病,身体状况已不如从前。退休之后,他的生活日常仍然总在锻炼、读书、思考、写作、做饭、打扫卫生、下地干农活之间循环,“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也不知道每天是星期几、几号,几十年如一日过着传统农民式的简朴生活”。
在治学路上,他只是想把学问做深做透,自甘寂寞,始终如一地按照自己的研究思路摸索前进,从不为潮流所动并坚持独立思考。他经常劝勉学生,要耐得寂寞,并一直秉持笛卡尔的行为守则:始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
陈云生觉得,要做到对宪法的“起信”,发挥其在真正意义上的安邦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为此,他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提出了建立“国家宪法日”和在人民大会堂专设“国家宪法陈列厅”的建议。
陈云生庆幸,如今自己在宪法和法学研究上之所以取得些许成就,端赖当时的语文老师的“不由分说”。“看来作为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不仅专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分,在学生人生道路上还可以提出最优选择的建议。”他说,自己至今都会想起那位可钦可敬的恩师,“是他指引我走上了最适合我发展的人生道路,师恩如山高似海深,铭记在心、永生难忘”。
在法学界,陈云生的身份非常特殊。1942年,他生于河北唐山专区平谷县(现为北京市平谷区),是乡村里第一个自主考上高中的学生、第一个大学毕业生,直至成为宪法学大家,被视为“从山窝窝里飞出的金麻雀”。
在中国学术界,有非宪法专业的学者认为宪法制国家的其他法律如民法、刑法都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应平等对待,制定其他法律无须依据宪法。“这种观念是缺乏宪理常识的表现。”陈云生认为,宪法之所以被称为“父法”“母法”,就是其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地位最高,制定其他法律必须依据宪法。因此,改革开放之初的法学重建是以宪法的重建为先,而宪法重建也必须首先确定宪法至上的观念。
因缘际会,自1982年起陈云生就跟随张友渔先生,为其起草了大量报刊文稿、书稿和讲话提纲等等。“当时张先生已经八十多岁,觉得我写文章比较耐看,所以喜欢找我帮他撰写文稿,然后由他修改,我也实际上承担了他的文字秘书工作。”陈云生说,作为唯一报考人,他通过了“没有竞争”的考试,成为张友渔的博士研究生,“既是张老的开门弟子,又是关门弟子”。
由于经费不足,学校还揽下了邻镇制鞋厂的一部分零活,缝制成品布鞋,“我的制鞋技术较好,就让我做了监督员”。陈云生回忆,尽管条件艰苦,但他始终努力上进,最后成为村里第一个自主考上高中的学生。
皇冠菠菜app法治站上新的历史坐标。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法治”一词前后被提及23次并有了新部署:“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治学期间,他经常劝勉学生上学期间要专心学习,毕业之后要认真做好学问,“这个社会总是要由有学识、有远见的人才能支撑起来的”。他觉得,过去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现在应该改为:“我为故我在”,“你之所以成为你,都是你自己做过的事造就的,个人自我实现、获得成功,总是要付出很大乃至毕生的努力”。
前述修正案不仅修改了“八二宪法”中的部分内容,还为中国宪法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课题,进而推动了宪法学的发展。针对宪法修正案,中国宪法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论证、释文和引申阐述性文章或专论,对修正案的意义和实质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陈云生在宪法学领域所从事的研究更为深广。在完成了《宪法人类学》和《反酷刑》写作之后,他又完成了《宪法监督司法化》的著作。如今,“宪法监督”议题仍是当下宪法学研究的热门。
1983年,陈云生迎来了另一件不期而遇的大幸事:国务院点名由几位泰斗级老专家以传统“师带徒”形式培养学术传承人。这些老专家中,包括号称中国法学泰斗的张友渔先生以及其他三位哲学、经济学和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他们分别是于光远、许涤新、夏鼐,老先生授命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自己的“门徒”。
自1978年国家恢复硕士研究生教育后,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空白状态随之凸显。进入新历史时期后,中国急需各方面的高等人才发挥骨干和栋梁作用。为满足这一需求,博士研究生教育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逐渐被提上日程。
1978年9月,陈云生如愿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报到,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共19名法学研究生。此次考研彻底改变了他个人及家庭的命运,也开启了专攻宪法学的治学生涯。三年之后,因成绩优秀,陈云生顺利毕业并留在法学所工作。
“这些分类和研究方向逐渐构建起了中国宪法学的学科的完整体系。”在此期间,陈云生还将其费时十年的思考凝结成《权利相对论——权利和义务价值模式的建构》一书,试图将经过承继和扬弃的法理和制度与本土优良的文化、道德和法律传统相融汇,从而尝试实现建构新的法律价值的观念模式和体系模式。
除此之外,他还针对普遍尊重宪法权威、认真贯彻实施宪法的要求,特别是在“宪法为什么是重要的”议题上,每年以特定视角撰文,发表了《宪法为什么是重要的》《再论宪法为什么是重要的》等专论,“希望有更多的宪法同仁参与进来,多在‘宪法为什么是重要的’这类入门的问题上做研究,并多写有说服力的文章和著作”。
2014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尽管公众已熟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还需深入理解其背后的立宪原理。”陈云生认为,当前中国法学界面临的任务是树立和重构宪法至上的理念和机制,确保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宪法学术界认识到要取得研究和教学进展,必须科学规范地界定宪法学的学科体系。与此同时,宪法学者们还提出了多个学科分类和研究方向,包括宪法社会学、宪法人类学、宪法政治学、宪法规范学、宪法阐释学和宪法史学等等。
但他始终认为,这些虚名并不重要,最重要的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学术不能脱离社会,也不能与政治完全隔绝,有一部分学者将自己主要的学术兴趣和注意力放在直接为现实的政治、法律服务上面,这本无可厚非。但也应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即并不是任何针对现实问题作出的研究报告、提出的改进意见,都应当或可能被有关的政治决策机构接受和采纳”。
提及求学经历,陈云生说:“少年时,每到夏天,我躺在野地上看着朗朗晴空,流星一个接一个,清晰可见的银河系,是那样的迷人,令人遐想。所以,填报大学志愿时,曾立志把第一志愿报考天文系,后来由于文理科分别科考,语文老师因觉得我作文比较优秀,‘不由分说’让我改考文科,天文学家也终归成了梦想。”
“此生只向学问去,道他读书情也痴。”从此,陈云生真正踏上了专攻宪法学业之路。作为“副产品”,此次读博还赋予了他一个符号性标记:中国有史以来本土培养的第一位法学博士。
1962年,陈云生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逐步涉猎政治、法学等科目,毕业后在广西从事司法、教育、行政等工作。1978年,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深造,开启了宪法学领域的专攻治学。后来,他又继续攻读著名法学家张友渔的博士研究生,成为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位法学博士。
陈云生的求学之路是从邻村新建的一所初中开始的。那时,北京平谷东部、南部、北部地区的孩子们都涌向这所学校就读。报到那天,他们看到的却是一片空地:没有教室,没有食堂,开学第一课就是挖地基、盖房子。半年之后,简陋的教室和食堂才算建成,当地村民的房屋成了学生们宿舍和厨房。“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六七岁的少年,每天清晨早起做饭,从未耽误早自习和上课学习。


 换一换
换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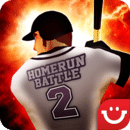




 皇冠菠菜app v3.2.5官方正式版
皇冠菠菜app v3.2.5官方正式版